这个话题类似美元的问题,但我觉得罗德里克的表述更好理解。但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
差不多十二年前,在一个夏天,我和朋友一起去了伊犁,哈萨克族的朋友热情招待了我,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哈萨克朋友的祝酒总是令人难以抗拒,他们并不会强迫你喝酒,但说完热情祝酒词之后,他们告诉你随意就好,但自己经常仰起头一饮而尽。然后无论是放声歌唱还是摇曳起舞都让人神往。这一切都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傻子,也只能站起来向大家祝酒,然后学着他们一饮而尽。再醒来就已经是第二天了。
当时伊犁对岸的哈萨克斯坦,正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我的哈萨克朋友和我说,哈萨克斯坦其实也希望中国能考虑转变一些当地的产业政策,我当时说,中国一向是不干涉内政想法,不愿意干涉别人内政,也不愿意别人干涉自己内政。这样的诉求我能理解但我不知道能否实现。
当时坐在我对面的朋友看着我说:当中国体量足够大的时候,中国的内政就可以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外交了。当中国的内政可以影响一个周边国家的产业时候,这到底是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还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杂糅呢?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样,我那一瞬间就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同时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
当我回到学校,读到了罗德里克写的《全球化的悖论》,我就非常感同身受。这本书的核心意思就是标题里说的
- 群众的呼声
- 自主的政策
- 深度全球化
这三个东西很难同时实现。在开头说的例子是第二点,一个全球化贸易关系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两个国家,彼此的内政会影响到对方的外交。也难免被彼此影响。
这点还有一个例子,在耶伦还在当联储主席的时候,她是比较全球化的,她知道美元实际上不止是美国的美元,而是世界的美元,所以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了问题,多多少少都是联储的问题。而鲍威尔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他更多觉得美元就是美国的美元。
其实说实话,以前的世界,是联储做事,然后北京跟着联储做事,等于是联储在一个完全基于本国经济数据的Mandate下做事,而北京跟着联储做事。2015年这个事情出现裂痕之后,耶伦和周行长一年内三次会谈,谈的就是这个问题,美国的货币政策外溢影响。最后双方其实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但可惜2016年年底Trump上台,历史从那里开始拐了一个大弯。
在2020年的风暴中,联储同样给世界很多央行提供了应急措施也是一个例子。美元是全球货币,所以全球的问题都是美元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2015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025年的中美已经开始了不可逆的脱钩。无非进展到了百分之多少而已。
我想这两个例子展示了什么叫做自主的政策和不能完全自主的政策。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深度全球化,同时希望自己保证政策自主权争取获得最大利益,那就不可避免会忽视一部分群众的呼声。
美国的MAGA群体是现在最鲜活的例子,过去的经济发展整体是划算的,但他们是代价。中国在2001-2021年的发展也有类似的事情。同样,一些深度全球化的国家,或者尝试深度全球化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越南,在保持了自己政策自主权的时候,不可避免忽视了部分群众的呼声。
我们还是用哈萨克作为例子。2013-2014年,哈萨克坚戈进行了大量的贬值以便稳定经济,哈萨克是一个资源出口国家,出口原材料,进口日用品。坚戈的贬值让哈萨克国家在出口原材料上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用来偿还先前的债务。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进口日用品的时候,就面临更多压力。
在这个例子里面,哈萨克不愿意退出全球市场,独立执行了贬值政策,但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受伤。
而最后一个就更简单了,如果一个国家深度全球化,同时完全按照简单多数原则决定自己的政策。那么因为深度全球化,他的政策往往失去自主性,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IMF对很多国家的援助都是带有条件的。这意味着例如曾经的东欧和南欧国家,他们选民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政府可以在一些方面作出回应。但这些国家的利率,汇率,财政政策必须被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不然欧盟或者IMF就会对他们做出惩罚。
意思是民众可以选择自己想执行的政策,但政府在落实其中一些的时候,会面对外部的掣肘。
但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全球化之前,世界的博弈往往是Have's和Have not的博弈,而全球化之后,多了一个国际市场。这其实就是个简单的三角博弈,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和一个对手站在一起,去干另一个对手。
然后在2016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讨论叫做菲利普斯曲线是不是失效了。当时实话说,我确实觉得学术的讨论非常不得其法。任何一个做过国际工程的人一秒钟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可以实现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因为当美国经济走弱,通胀走低的时候,新兴市场收入减少新兴市场的失业率走高。当美国经济走强,通胀走高的时候,新兴市场收入增加失业率走低,同时低价出口美国帮助美国压制出口。这个例子让我明白了国际的资本流动在合理的时候是可以缓解国内矛盾的。但前提是国内分配要做好。因为美国低通胀低失业率,并不是所有地区的低失业率。
在罗德里克的书里面,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1980年的超级全球化退一步,因为这个超级全球化,同时压制了国内群众的呼声和国内建制派的政策空间。如果能退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么群众的呼声和自主的政策有更多空间。
- 在1945-1971年的世界,全球化并不是为了利润本身,而是相当一部分为了服务就业。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苏联。
- 固定汇率而不是浮动汇率,让各个国家不用无止境让渡自己的政策自由
- 资本无法自由流动,同时国家保留了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这等于是顶层和基层一起消灭国际资本
- 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路径,不严格要求自由化
可以看到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说法,都是让全球自由资本,让步给本土资本的利益。时隔14年,罗德里克的说法现在看起来就更有那个样子了。对于美国,Trump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个改革对美国经济到底负面冲击多大不好说,但不管对美国经济负面冲击是多少,对美国市场的冲击都要比经济更大。
那么北京会如何,北京过去执行的是深度全球化+自主政策。而2021年之后开始转向变成深度全球化+群众的呼声。那么未来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自主政策可能要有所让步,或者说,中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政策调整,会影响到自己的贸易伙伴,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去让双方的利益能够互补。这是战后美国做的事情,而WTO,联合国,IMF都只是这个体系里面的部门而已。美国曾经建立的这个系统其实是非常牛逼的,曾经在中东的时候,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所有你们底层人民都在看美国的电视台喝可乐,很多你们的高层都或多或少亲美,而你们竟然被美国当作是敌人且把美国当作敌人。这是如何做到的?
而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系统开始崩塌,而且速度很快,这其中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所有的危险也都是机会,如果北京能建立一个新的政策体系,一个新的规则系统,去公平分配所有李嘉图理论带来的利润。也许就有机会建立新的世界。这也是北京始终坚持开放的原因,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做零和博弈的结果总是一方输一方赢。而在一个开放系统里面,这个零和博弈至少不用全部发生在体系内部。
我确实觉得,就像之前东南亚那篇文章里写的,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系统开发,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
回答上一篇文章的最后,过去40年最好的机会是深度全球化,压制一部分国内声音,压制一部分自主政策带来的机会。而未来对北京而言,我不知道全球化会不会比过去更好,这是个未知数。但我知道群众的呼声从2021年开始被更多听到的故事不会马上结束,而政策的制定更多考虑外部性而不是纯自身,则是这个硬币的另一面,这个事情一些技术的原因开始很慢,但他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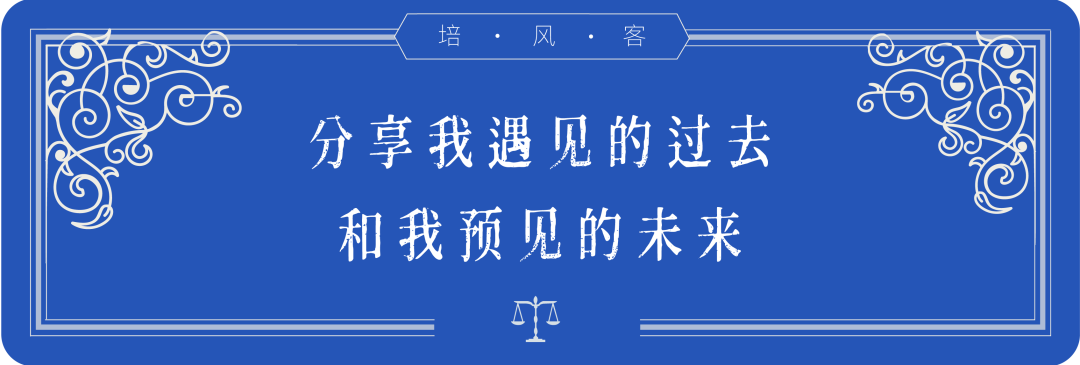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