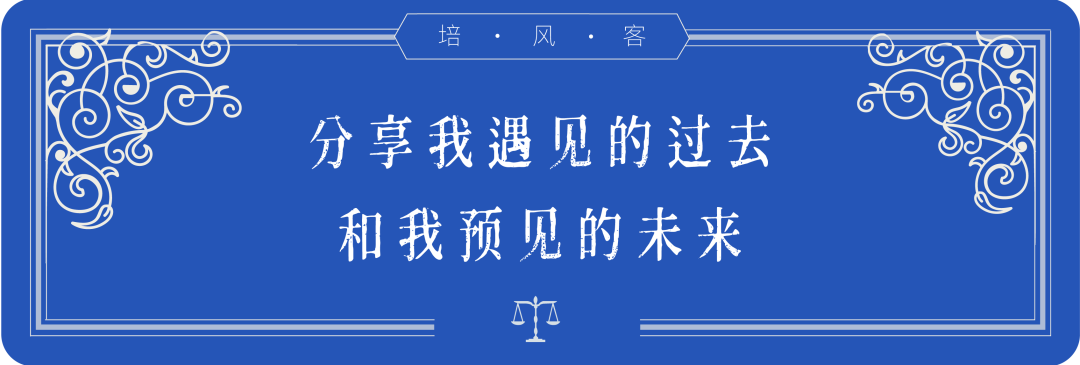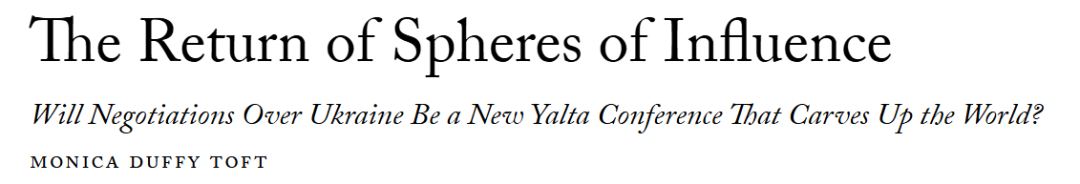20250701 - 地缘政治研究 - 影响力范围理论
相信细心的读者早就发现,从去年开始,地缘政治的研究就成为了半年或者季度展望里面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对政治的兴趣和研究由来已久,但真的能有大片的时间去认真沉淀学习,也是在过去一年才有机会。而我没过多久,就发现学习这个东西确实可以举一反三,联想学习法非常有效。
政治家就像股票,有行情好的有行情不好的,有周期性的有趋势性的。支撑股价的因素主要是EPS和PE,而支撑政治家的是Publicity和Popularity,其中前者的研究真的很像EPS的研究,它相对可以量化,划分选区和划分业绩单元其实类似。后者的研究就很像PE的研究,他不太可以量化,不同时期,同一选区的人,喜欢的东西也不同。
牛逼的政治家就像是牛逼的股票,EPS非常稳健,然后PE可以穿越周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都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当然,这有些时候被叫做圆滑。
在市场的研究里面,虽然我已经有了新欢,但旧爱一直是经济周期的研究,这是我曾经最开始了解经济的入门老师。那么在政治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因为我有学习路径的依赖,所以我也是先从这里开始的,叫做政治理论。
长周期的政治理论,无论是领导力理论(Model of leadership),还是帝国的兴衰周期,都有点类似康波理论。而更关注拐点时刻的Power Transition Theory,就很像明斯基时刻,而短期的选举周期和民粹主义,类似那种14-42个季度的经济短周期。
所以如果说2025年7月的我,比2024年7月的我,最大的进步或者变化叫做,我觉得如果在经济上,你提出了一个周期性因素,或者结构性因素,那么你也必须在政治上,提出一个对应的周期性因素,或者结构性因素。不然你的故事就只讲了一半。而且缺失的可能还是重要的那一半。
我想这就回答了开头提出了问题,为什么现在我把地缘政治总是放在展望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这样的文章印尼 - 政治研究 - 性格即命运(佐科和钟万学) - 003,这相当于个股研究。而今天的文章就像是经济周期的分析。其实在之前几个月我写过这个内容,但我觉得今天有必要重新提一下。
我们先从一个新闻开始
昨天Trump在接受Fox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中国对我们做了很多不友善的事情,为什么你还要和他们谈交易,Trump直接说,你觉得我们就没对中国干这些坏事么?然后记者直接无语了。
和每次这种新闻一样,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Trump是一个素人,然后什么都不懂。但这种回答不是正确答案,之前说了,一个获得了7000万以上选票的总统,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
让我们先从这个新闻走开,回到一个旧文章
在大概三个月前,美国外交的权威杂志Foreign Affair发了一篇文章,叫做
影响力理论的回归?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讨论已经是去年,而今时今日,在秋天各种可能的中美俄三国领导人见面场景下,这个理论从未如此真实。
我相信它是对的,我相信影响力范围理论已经回归了,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之前我讨论东南亚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个理论,我简单用我的语言总结一下这个理论
- 在影响力范围内的失败不可接受
- 在影响力范围外的成功不可持续
而胜利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稳步,持续扩大影响力范围,第二是,准确判断不同时期的影响力范围,保证在范围内的胜利,然后不要过度追求范围外的短暂成功。
这几乎可以解释过去几个月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无论是Vance在德国几乎背刺德国整个政治圈,还是之后Trump在北约问题上的峰回路转,无论对于丹麦和加拿大的诉求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同时很关键的,如果说别的地缘理论中国可能多少有些陌生,这个影响力范围理论,中国太熟悉了,这就是换皮的朝贡体系。
Foreign Affair的很多文章充满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但他们的理论功底依然深厚。影响力范围理论是一个古老的理论,它更多发生在殖民地时期,当然这里我忍不住想对比一下,对于东方文明更熟悉的朝贡体系,和对于西方文明更熟悉的殖民体系。因为如果回到这个影响力范围的框架,我相信这两个理论都会重新拿出来。
朝贡体系和殖民体系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构造了一个等级结构,宗主国或者天朝都是高于藩属国和殖民地的。也都存在严重的实力不对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是如此。并且伴随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授予。
初看起来非常类似,但内核完全不同,朝贡体系用粗俗的话说叫做
- 你叫爸爸,爸爸很高兴
- 你不叫爸爸,爸爸无所谓
- 你打爸爸,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朝贡体系其实根本不需要太多从藩属国的经济利益,甚至很多时候中国给藩属国的礼物远大于他们上贡的。朝贡体系中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臣服,证明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这种思路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只不过如果说很多年前,这种朝贡体系,追求的是边境的安稳,而今天中国的货物,已经卖去了从未设想过的远方。这对于中国的文化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殖民系统需要的更多是经济利益运回国内。
扯远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国际政治里面,似乎存在一种复古的潮流,Trump的经济政策,对于关税的热爱更类似150年之前而不是5年之前,我们似乎回到了重商主义的年代,而外交政策也从1980年之后的时代,回到了殖民地时代,sphere of influence这个词汇大概是140年前的柏林会议热门词汇。
当然,你可以从时间轴去说,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但要警惕,历史往往是螺旋前进,所以在短期你其实很难知道哪个方向是前方。
更准确去说,这是当美国开始追求恢复过去世界的荣光时,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找解决方案的一个时间段。当过去世界的增速不可复制的时候,保守主义第一个站出来,告诉大家说,回到过去也许可以找到解药。这点不要嘲笑美国人,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也都有这个阶段,2016年居民部门上杠杆,央行和联储三次会议尝试达成协调,包括到现在,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相信,回到过去一切都可以好起来。
过去40年,全球秩序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主导,当美国主动拆掉自己的全球秩序的时候,尤其是以一个保守主义底色去拆除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并不会对此有太多异议,甚至会隐约有一种知音感和暗喜。
这种拆除,在今年的市场,今年的外交上都已经有了体现,所以我们要想下一步,秩序是一个短期可以被打破,但长期总会有人尝试建立的东西,无非是谁主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是美国重新构思对世界的安排,欧洲体会到了危机,日本尝试用通胀化债,所以每一个现在出现在台上的日本政客可能都是一个悲剧角色,这也是一些可怜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在西方的语境里面,中国和俄罗斯扮演的是类似的角色,但这个问题你去问俄罗斯和中国人,得到的结论肯定是迥异的。中国并没有想好,可能也没有准备好去建立一个全球秩序。还在艰难的思考和探索中。
在这个混沌时期,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的是,当世界变得更加丛林主义,影响力范围理论会更多出现。而中国,美国,俄罗斯会努力扩大自己的范围,日本和欧洲可能需要做好准备,布林肯的警告可能是真的,你不在餐桌边,就在餐桌上。
而中国和美国思路的不同,在很多地缘政治的边界区域。如果说冷战的核心是莫斯科的眼光透过欧洲看向大西洋对岸的华盛顿。那么这一次沸腾的大洋可能是太平洋,而地缘的焦点可能是东亚和东南亚。此时此刻,我相信我上面说的这些东西,也会在东京,在首尔,在吉隆坡,新加坡和雅加达被讨论。中国的朝贡体系需要的是名而不是财,甚至中国愿意以一个合作的态度去创造更多利益,美国的体系更多要求是实打实的利益,综合考虑之后,这些国家会做出符合自己产业的选择。
在昨天和Mike的播客里面,我听他说产业升级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因为你搞一个超市,搞一个零售商去东南亚,刚开始你可以做,过几年这东西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当地人学会了就把你赶走。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话题,持续的科技创新,持续的产业迭代,给当地带来一波一波的产业升级,然后通过过程中的设计,绑定利益,分享利益,这是未来几年中国在东南亚会做的事情,也是一切的关键。
这点其实很有中国哲学的影子,中国过去做得最好的是制造业赚钱,现在扩张也是靠这个,但与此同时,在国内打造一个更加均衡的经济体,加上对外的制造业扩张,可能是中国的两条腿走路。
硬币的另一面,美国过去做的最好的是服务业,美国对外扩散影响力靠的也是这个,但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内补足一些制造业的短板,加上对外的服务业扩张,可能是美国的两条腿走路战略。
这个过程中,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各自的战略选择会带来很多机会。理想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拿到中国的制造业资源和美国服务业的资源。就像冷战时期很多地区充满了摇摆,但都拿到了实打实的利益。
之前我把我写的2025H2战略展望给一些朋友批判的时候,我得到了几个宝贵的意见,认为我在下面四个地方可以进步
1,中美周期性兜底意愿的边界和代价
2,中国腾挪的效率和风险
3,周期性和结构性拐点的市场判断
4,第三方角色的缺失
其中前面三点我觉得都是可以简单加上去的,第四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但也是缺失的,就是欧洲,日本,印度,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如何应对中美的这种竞争。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于是就有了这个文章,和它的后续,有了这些内容,我觉得才会是一个饱满的讨论。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