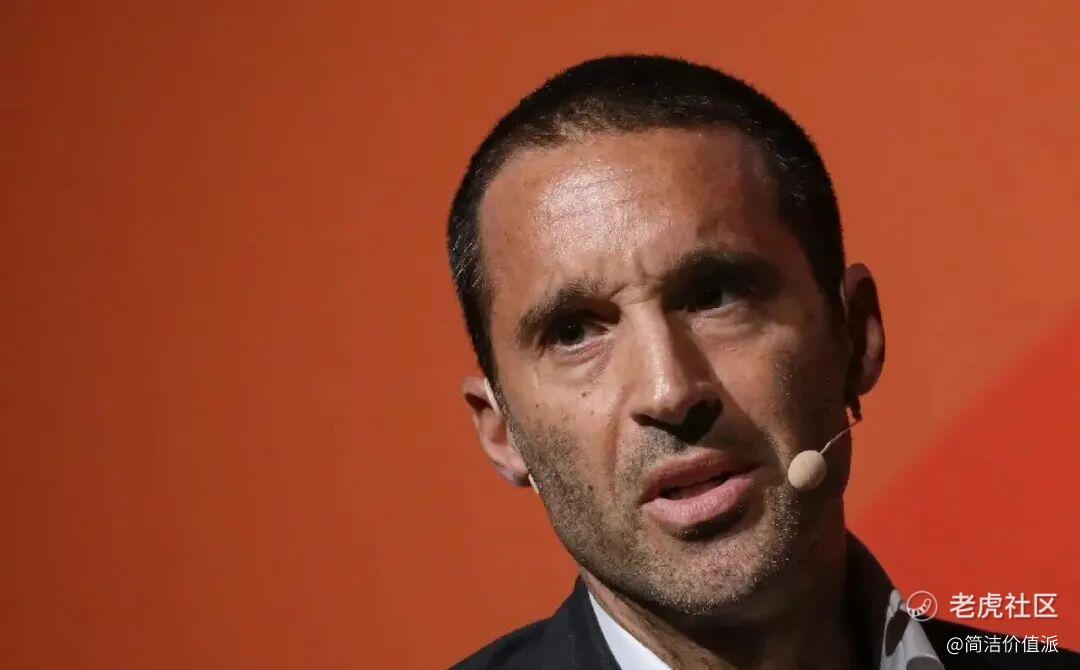多空皆能:D1 Capital的投资逻辑全景
导读:
这篇访谈展示了D1 Capital创始人丹·桑德海姆对投资方法论、风险管理与行业趋势的深度思考。
不同于多数基金经理,他在多空策略上同样游刃有余——从最初因一份做空报告入行,到后来经历GameStop逼空的惨痛教训,他坦承风控才是投资生涯中最核心的课题。
访谈中,他强调:面对市场短期波动,要区分基本面变化与情绪噪音;前者需果断修正,后者则可能是加仓良机。
在资产配置层面,D1同时布局二级市场与私募股权,从早期投资SpaceX,到押注OpenAI、Anthropic等人工智能公司,他的逻辑始终是:寻找长期结构性趋势下的优质标的,以合理价格买入并让时间复利。相比单纯追求短期套利,他更关注如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技术浪潮中占据先机。
访谈最后,他提到巴菲特式的思维转变——从“烟蒂股”到伟大企业——并提醒年轻投资者:情绪是最大的敌人,阅读与学习是最好的护城河。整体来看,这是一份兼具实操经验与战略远见的对冲基金思维全景图。
以下是访谈正文,有删减:
大卫:那么请介绍一下绿光资本具体做什么?它是一家价值投资机构,还是其他类型的投资机构?
丹:我们是价值投资机构,既做多也做空,同时也会进行宏观层面的大趋势投资。但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买入我们认为被低估、且会因价值回归而表现良好的资产;同时做空我们认为被高估的资产。
大卫:如果你要研究一只准备买入的股票或一家准备收购的公司,你通常会花多长时间?
丹:如果是我们从未研究过的公司,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多数公司我们过去都研究过;但若是全新的公司,通常需要我们大约3到4周来完成这类工作。
大卫:你们也会和CEO沟通一两次,对吗?那你们如何避免接触到内幕信息?
丹:是的,我们尽量与每一家我们投资的公司的CEO沟通,同时我们有合规把关。我们的总法律顾问会参与把控,而且大多数上市公司本身也很清楚哪些内容可以说、哪些不能说。
因此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大卫:你们是少数(但并非唯一)既做多也做空此类股票的大型机构之一。做空在很多方面更复杂,除非你的对冲做得非常充分。为什么你们对做空感到游刃有余?
丹:我入行之初就是做这个的。我拿到第一份工作的原因,就是我写了一份做空报告。我喜欢做空股票,我觉得这在智力上很有挑战。
从业务角度看,擅长买入的人很多。但擅长做空的人较少,或者说愿意做空的人更少,因为做空更难、压力更大,而且长期来看利润率更低。
大卫:你们曾参与过一次非常知名但结果并不理想的做空案——GameStop,对吗?
丹:没错。
大卫:看起来像是有人在操纵什么,使得一家本可能适合被做空的公司突然变成了“英雄式”的大涨股。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如何应对?
丹:非常痛苦。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几周。我也希望那段时间将会是此后所经历的“最艰难”。不幸的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被做空的股票在两周内上涨300%或400%的情况。
按历史数据来看,这甚至超出了五天标准波动范围。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我们当时确实没有为那种情况做好准备。
结果我们在明知是最糟糕的时点,仍被迫在最糟糕的时点平掉了所有头寸。但如果那种情形再持续几周,带来的痛苦与损害会更大,所以我们只能这么做。
大卫:那么在对冲基金世界里,当你建立多头或空头仓位后几乎一开始就逆着你走,你会说“我错了,立刻止损”,还是会说“我比市场更懂,等等看,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你一般等多久才会承认市场比你更懂?
丹:归根结底取决于研究本身。
有时股价波动确实有原因——比如公司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投资逻辑,并可能调整仓位。
但很多时候,股价波动与企业经营或基本面无关。这种情况下反而是我们加码持仓的机会。
大卫:如今你们以团队协作做投资决策时,组织内部会追求共识吗?
如果有人说“我不同意”,而其他人也不赞同那个人的观点,会怎样处理?
除了你之外,是否允许单个人就把一个投资按下不表,还是只有你有权力否决一笔投资?
丹:我们的流程并不是设置多层级去审批或否决投资。
我们是协作文化,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即使意见不一也没问题——通常不会是“强烈同意”或“强烈反对”的两极化立场。
更多是对前景的判断:要么觉得这是很棒的投资,要么觉得“还可以”。最终由我来听取各方意见并做出结论。
大卫:在你的业务中,当你说一项投资“还可以”或“不错”时——你预期的回报率大概是什么水平,比如说年化20%吗?
最终拍板时,你希望的年化回报是高于20%,还是15%,你具体在看什么指标?
丹:这取决于公司的风险特征。如果是大盘、高质量的公司,三年期预期内部收益率(IRR)做到20%就足够了。
如果风险更高(比如产品还处早期或杠杆更高),那么我们会要求更高的IRR,接近30%。
大卫:据我所知,你一直是SpaceX的重要投资者。SpaceX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丹:是的。
大卫:对冲基金通常买入或做空上市公司股票,较少参与私募股权,因为早期私募是完全不同的玩法。私募市场的估值来看,SpaceX相当成功。但你既投公开市场也投私募,对吗?
丹:没错。我想你们进得比较早——我们最早大概在六年前投资的。现在的估值大概在数千亿美元。我们加权平均的入场估值大概在300–400亿美元。
大卫:在这种投资里,如果公司的创始人或CEO进入政府、不是每天管理公司,你会担心吗?我知道他们有很强的二把手,但这会不会是个需要担心的问题?
丹:对我来说,这不是担忧点。
我认为伊隆显然是跨时代的人才。我当然希望他把全部时间都放在SpaceX,但他也打造了一支出色的团队,足以胜任公司的日常运营。
在我看来,他真正擅长的是在关键时刻介入并解决难题,而不一定需要每天盯着所有细节管理。
大卫:我知道你一直大力支持人工智能,认为它将真正改变世界。那你在投资时,会投人工智能领域的小公司,还是更倾向于投知名的大公司?从赚钱角度看,投资人工智能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丹:很难说有“最佳方式”。就和我们业务模式最匹配的路径而言,我们投资了OpenAI和Anthropic,这两家都是领先的大语言模型公司。并且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由AI驱动的公司出现投资机会。
大卫:但你们不会去找下一个“年轻版Anthropic”之类的超早期项目,对吗?那更像是风投的活儿。
丹:对,我们不会在非常早期阶段出手,也不会去和风投竞争,在公司成立一两年内就投。我们更倾向于在公司成熟一些时投资。
大卫:除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下一波值得你投资的技术浪潮?比如量子计算之类的?
丹:是的。我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甚至更久,AI仍会是最重要的技术。但就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你会看到很多由AI催生出来的领域:比如机器人、还有生物科技创新。我相信会有大量由AI驱动的方向本身演变成独立的技术革命。
大卫:D1 Capital Partners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丹:灵感来自“Day One(一日如新)”这句话——贝索斯经常用它来描述他对亚马逊的思考。创立公司的第一天有创业的能量、动力和开放式的增长机会。我不希望公司变得迟缓、官僚,所以每一天都应该像“第一天”。
大卫:现在公司多大了?是哪一年开始的?
丹:公司成立于2018年。今年夏天就满七年了。
大卫:那你起步资金是多少?
丹:大约50亿美元。
大卫:问:如今你管理大概多少?
丹:230亿美元。
大卫:现在公司的总部在迈阿密?
丹:算是迈阿密和纽约的双总部
大卫:你们仍然专注于一贯擅长的方向——主要是股票,而不是宏观交易,对吗?
丹:股票——更准确说,是对公司的基本面研究,并通过二级股票和私募股权两种方式来表达。
大卫:你们现在有多少名投资专业人士?
丹:大约30人。
大卫:最终决策都由你来定吗?作为CIO,别人能独立做一定规模内的投资,还是所有决定都要过你?
丹:D1是合伙制,合伙人在一定额度内可以自主投资。但大约95%的投资决策由我来做。
大卫:募资路演需要你亲自去讲吗,还是凭声誉就行?
丹:不,我们不会只靠声誉吃饭。我喜欢亲自去见客户、讲清楚我们的故事。客户越了解我们,关系就越好,长期黏性也更强。
大卫:许多学生说想进D1这样的平台,觉得必须学理工科,不能学英文或历史。你们只招STEM专业吗?专业背景重要吗?
丹:我发现具备强分析能力的人很多,但能把观点清晰表达,尤其是书面表达的人更稀缺。所以我们对专业不设限,但要求既具备分析和量化能力,也能良好沟通。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口头或书面清楚地陈述投资论点,否则会很难。
大卫:你投资生涯中,得到的最佳投资建议是什么?
丹:大概来自巴菲特的启发。他谈到自己的演进:最初买“烟蒂股”,后来意识到创造价值的最佳方式,是以合理价格买优秀企业,让时间复利。刚入行时人们常找远低于公允价值的标的;转变为以接近公允价买伟大企业、靠长期复利,这种思维转变非常关键。
大卫:你认为普通投资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丹:情绪。房价跌了你不会立刻恐慌抛售,但股票交易太便捷,人的贪婪与恐惧更容易主导决策。
大卫:对刚起步的年轻投资者,你会给出哪些关于创业或职业发展的建议?
丹:自立门户很难,通常是错误选择——机会只有一次。先尽可能多读书。若偏好基本面投资,巴菲特的东西很棒;其他方向也要广泛阅读。然后进入你能进入的最好平台,向资深人士学习。这份工作需要终身学习。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