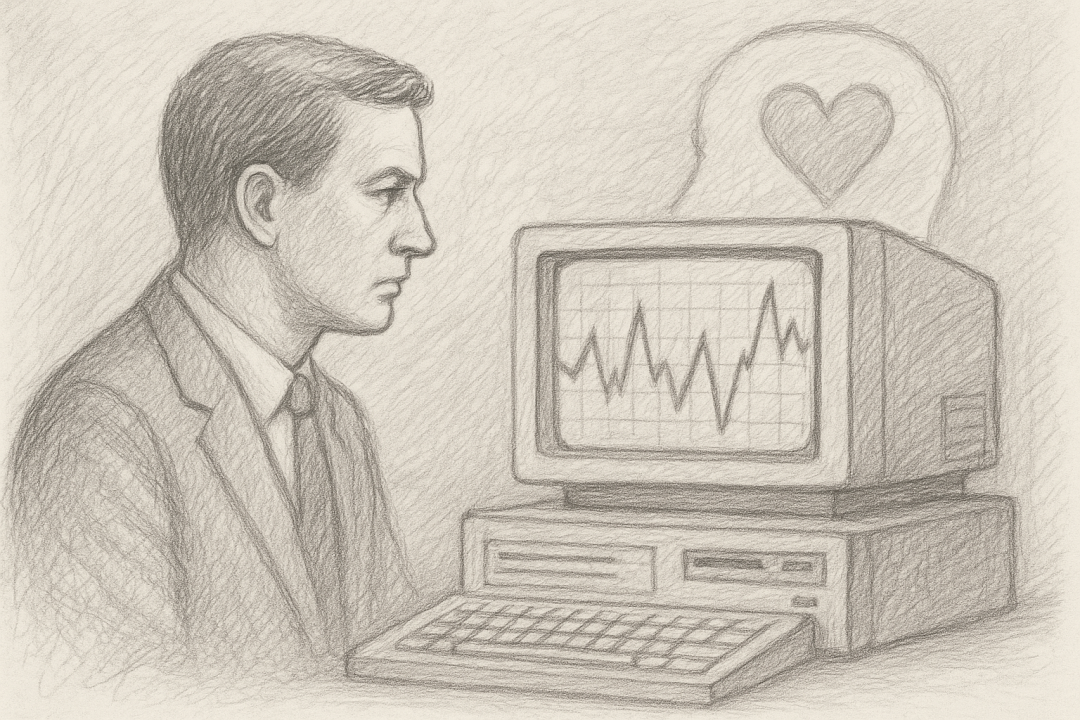AI能预测人心么?
1960年,一个叫 Simulmatics 的公司在美国诞生。它的创始人叫艾蒂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政治学家,信奉“只要数据够多,人类行为就能被预测”。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硅谷的祖父”,他们最早提出的口号是——“用模型预测人心”。
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肯尼迪的竞选团队。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遇上了资深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为了缩小差距,增加自己的胜算,肯尼迪团队找到了Simulmatics,希望借助计算机和民调数据预测选民行为。当时麻省理工教授普尔与广告人爱德华·格林菲尔德和心理学家罗伯特·阿贝尔森共同创办Simulmatics公司。他们从盖洛普等民调中提取十万份问卷,用IBM打孔卡录入,建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政治数据库。Simulmatics把选民分成480个“心理单元”,比如“中西部农村、低收入、新教女性”,又把选举议题划为五十种变量,如“就业”、“通胀”、“种族”、“宗教”等。所有这些数据被录入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IBM 704计算机。
1960年8月,肯尼迪团队正式雇用Simulmatics。公司连夜赶制报告,管理层在8月25日带着成果在罗伯特·肯尼迪(注: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的办公室汇报。报告名为《劳动节前的肯尼迪》,建议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中多谈经济与就业问题,以吸引北方工人,同时避免过度强调民权,以免失去南方白人。报告还指出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在某些州(尤其是南方和中西部保守地区)可能引起选民反感,应谨慎处理、避免成为竞选焦点。这些建议后来被肯尼迪竞选团队采纳。
1960年选举夜,美国的CBS电视台在IBM 7090上实时模拟选情,计算结果预测肯尼迪将以49.7%对49.5%险胜。最终结果几乎和预测完全吻合。Simulmatics公司宣称“我们的模型预测了胜利”,媒体称它为“能够预测人心的计算机”。无论功劳是真是假,这场合作让Simulmatics和其创始人普尔声名鹊起,也让他产生一个危险的想法:既然计算机能预测选票,为什么不能预测一切?
于是,他开始把“政治模拟”变成“社会预测”。
肯尼迪胜选之后,Simulmatics 认为他们迎来了“数据黄金时代”。普尔和格林菲尔德决定把政治模型商业化,向美国各大公司推销“用科学预测消费者”的理念。他们设计了一套名为 Media-Mix 的程序,号称能通过模拟三千个虚拟消费者的反应,预测广告在不同地区、不同媒体上的效果。不少大公司,比如雀巢、柯达、联合利华等都短暂的成为公司的客户。Simulmatics 的团队甚至搬到纽约第五大道办公,试图与广告行业的巨头们平起平坐。
然而,很快他们发现商业世界远比政治复杂。首先,广告公司早已有几十年的消费者研究经验,内部也在飞快发展自家的“数据科学”部门。像 BBDO、J. Walter Thompson、Young & Rubicam 都建立了自己的市场数据库,比Simulmatics掌握更多真实消费者资料。其次,Simulmatics 的模型过于学术化,费用昂贵,而且运行缓慢。一次模拟往往要花上几天才能得到结果,而广告客户则希望即时反馈。几年下来,由于客户续约率低,资金链紧张,公司现金流迅速枯竭。到了1963年,Simulmatics 已经欠下数十万美元债务,大部分员工被裁撤,只剩普尔和少数技术人员维持运转,公司濒临解散。
然而越南战争的爆发,又给Simulmatics带来新的生机。
1966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希望用科学方法“优化战争”,就好比企业优化生产线那样。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在“敏捷计划”(Project Agile)下拨款给Simulmatics,要求它建立一套“心理战数据模型”,找出哪些越南村庄最容易倒向越共。
普尔与ARPA顾问西摩·戴奇曼(Seymour Deitchman)领导项目,心理学家沃尔特·斯洛特(Walter H. Slote)和研究员安·温斯顿(Ann Penner Winston)被派往越南南部农村,挨家挨户发问卷做调查。问卷中的问题非常细致,比如他们问被抽样的越南农民:你最信任谁?谁最有影响力?你认为越共在村里有多少人?你愿意为南越政府工作吗?然后这些答卷被运回美国,经由IBM 7090输入分析。Simulmatics陆续发布报告《越南的交流与态度》,试图用统计方法量化“民心”。
一个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乌龙是,这些问卷竟然没有被匿名或加密,因此很多在问卷上被写下的名字落入越南军队和地方官员之手,成为“嫌疑名单”。在后来发生的“黑河事件”中,一批受访的村民被越共或南越特警抓捕甚至处决。美国记者沃德·贾斯特(Ward Just)讽刺道:“美国人用计算机数人头,越共用步枪数死人头。”
1967年底,ARPA审查认定Simulmatics报告“无科学价值”,计划随之被废弃。普尔在信中写道:“我们以为在研究人性,其实是在制造敌人。”战争的数据化实验,就这样以惨剧收场。
但Simulmatics并未收手。1967年,美国国内爆发种族骚乱。底特律、纽瓦克、罗切斯特等城市陷入火海。普尔和哈佛教授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可以用模型预测暴乱。
罗切斯特市政府成为第一个客户,Simulmatics派出六人调查小组,由彼得·舒尔曼(Peter Shulman)带队,其中包括社会学家、记者、小说家与黑人社区成员。他们在街头穿着军装访谈居民,仅一周之内就随机采访了80人,其中不少人正在制造燃烧瓶。接下来,舒尔曼亲自手写报告,预测“暴动将在7月23日晚上11点爆发”。报告送到莫伊尼汉手上后,他立刻通知州长加强戒备。果然,当晚罗切斯特出现小规模骚乱,Simulmatics大肆宣称“模型预测成功”。
这次预测成功的“奇迹”,让公司赢得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设立的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合同,研究全国暴乱的成因。Simulmatics获得22万美元资金,派人前往底特律、纽瓦克、亚特兰大等七个城市收集采访数据,又搜集15个城市的报纸、电视和广播报道,将每条新闻按“愤怒度”从1到9编码输入计算机,试图找出暴乱的规律。
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报告负责人索尔·沙内勒斯(Sol Chaneles)伪造学者名单;社会学家库尔特·朗(Kurt Lang)批评数据“粗陋到不可容忍”;莫伊尼汉本人劝舒尔曼“赶快离开那里”。最终克纳委员会宣布Simulmatics报告“无任何研究价值”。1968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建造“联邦暴乱监控中心”,希望用计算机预测社会动荡。普尔剪下该报道并贴进笔记本,坚信“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成功”。
但他期望的下一次的成功,再也没有到来。
1970年8月26日,Simulmatics在纽约地方法院宣布破产。那天正是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五十周年纪念日,五万名女性在街头游行,要求平权和结束越战。而仅仅在几条街之外,公司联合创始人爱德华·格林菲尔德的债权人(和情人)娜奥米·斯帕茨正在提交破产申请,试图追回自己为情人投入的最后一笔贷款。
Simulmatics的垮台并非偶然。首先是名誉扫地。越战项目被批为“把学术当作战争武器”,即他们以研究为名,服务军方支持战争为实,因此遭到学界和学生公开抵制。普尔在麻省理工主持“剑桥计划”时遭左翼学生围攻,被贴上“军方走狗”标签。其次是资金链断裂。政府合约全部终止,公司在波士顿、纽约和越南西贡的办公室相继关闭。格林菲尔德继而陷入酗酒和负债的恶性循环,试图以新商业项目“计算社会舆情系统”自救,却无人问津。1969年底,公司账上只剩不到500美元。
为了应对公司的不景气,普尔试图引入新管理层重组未果。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有巨额亏损可以抵税,却没有未来可以抵扣。”到了1970年,越南战争失败、社会动荡、种族冲突接连爆发,人们发现这些计算模型根本无法“预测人心”:模型既没赢得战争,也没解决贫困与不平等。于是,学界和媒体开始反思这一整套信仰,把它称为“冷战神话”(Cold War Myth):一种过度崇拜科学理性、幻想技术能掌控社会的集体幻觉。
站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Simulmatics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段被遗忘的寓言故事,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反思却完全没有过时。每当我看到某家量化基金声称“用AI战胜市场”,某个科技公司宣称“用算法预测消费者”,某个政客说“用数据治国”,我就禁不住想到Simulmatics:那股熟悉的自信又回来了。
这种想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海量的数据让人产生一种能够”掌控一切“的幻觉,但我们人类本身往往是最不可预测的。
这句话在投资世界里尤其成立。过去二十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源自同样的幻觉:即相信模型可以预测一切,并完全控制风险。2008年,华尔街的数学博士们用高斯模型打包垃圾债CDO,宣称能“精确计算风险”,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2022年,一批AI对冲基金声称自己能进行所谓的“情绪交易”。简单说来,就是让机器去“读懂市场的情绪”,比如分析新闻标题、推特帖子、分析师报告,甚至YouTube视频的语气,来判断投资者是兴奋还是恐慌,从而自动买卖股票。比如某些模型会追踪关键词“bullish”、“crash”、“panic”的出现频率;一旦检测到乐观词汇激增,就加仓;如果负面词汇暴涨,就减仓。还有基金试图从Reddit的热门贴文或TikTok热度中预测散户的集体情绪。
这些想法听起来很聪明,但现实往往很残酷。2022年初,美股和加密货币市场先后暴跌,这些AI模型却仍在根据“正面情绪信号”买入,因为算法看到的只是语言,而不是恐慌的人。机器以为投资者还在兴奋,结果市场几天内崩盘,模型集体失灵。
这场“情绪交易”实验告诉我们:算法可以识别文字,却无法感知情绪的温度。它能读懂“恐惧”这个词,却无法体会真正的恐惧。
这种幻觉,在今天的AI热潮中让人感觉尤其眼熟。ChatGPT 的发布让全世界兴奋不已,几乎所有人都在谈“人工通用智能(AGI)三年内实现”。投资机构把它当成新时代的淘金热,资金如潮水般涌入;从硅谷到中关村,谁提到“AI”,股价就能涨。Google 推出 Gemini,Elon Musk 宣布 FSD 自动驾驶“很快实现完全无人”,特斯拉的“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在舞台上比划两下,就能让市值增加上千亿美元。这些现象让我感到:资本市场像极了1960年代的Simulmatics:满怀信心、充满幻觉,坚信只要算法够聪明,人类的复杂就能被解构成公式。
但人类社会,尤其资本市场,从来不是线性系统。它由贪婪、恐惧、模仿、情绪构成,而这些变量永远无法被完全量化。ChatGPT能写诗,却不懂悲伤;能生成投资报告,却不会在亏钱时心跳加速。模型可以优化效率,却取代不了判断与责任。我们当然需要AI,需要数据,但它们是工具,而不是真理。数据能放大智慧,也能放大愚蠢。若没有理性与边界的约束,人类在AI面前的盲目崇拜,迟早会重演Simulmatics的结局,在自信的掌声中走向失控。
真正的投资智慧,不在于预见未来,而在于洞察当下。机器可以算尽千条路,却不懂人心一念间。想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靠的不是预测未来的算法,而是理解人性的定力与洞察。
参考资料:【1】Jill Lepore, If Then: How the Simulmatics Corporation Invented the Future, W. W. Norton, 2020.【2】Philipp Carlsson-Szlezak & Paul Swartz, Shocks, Crises, and False Alarm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24.【3】Ben Inker, Catherine LeGraw, John Pease, John Thorndike, It’s Always Darkest Before the Dawn, GMO Research, 2020.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