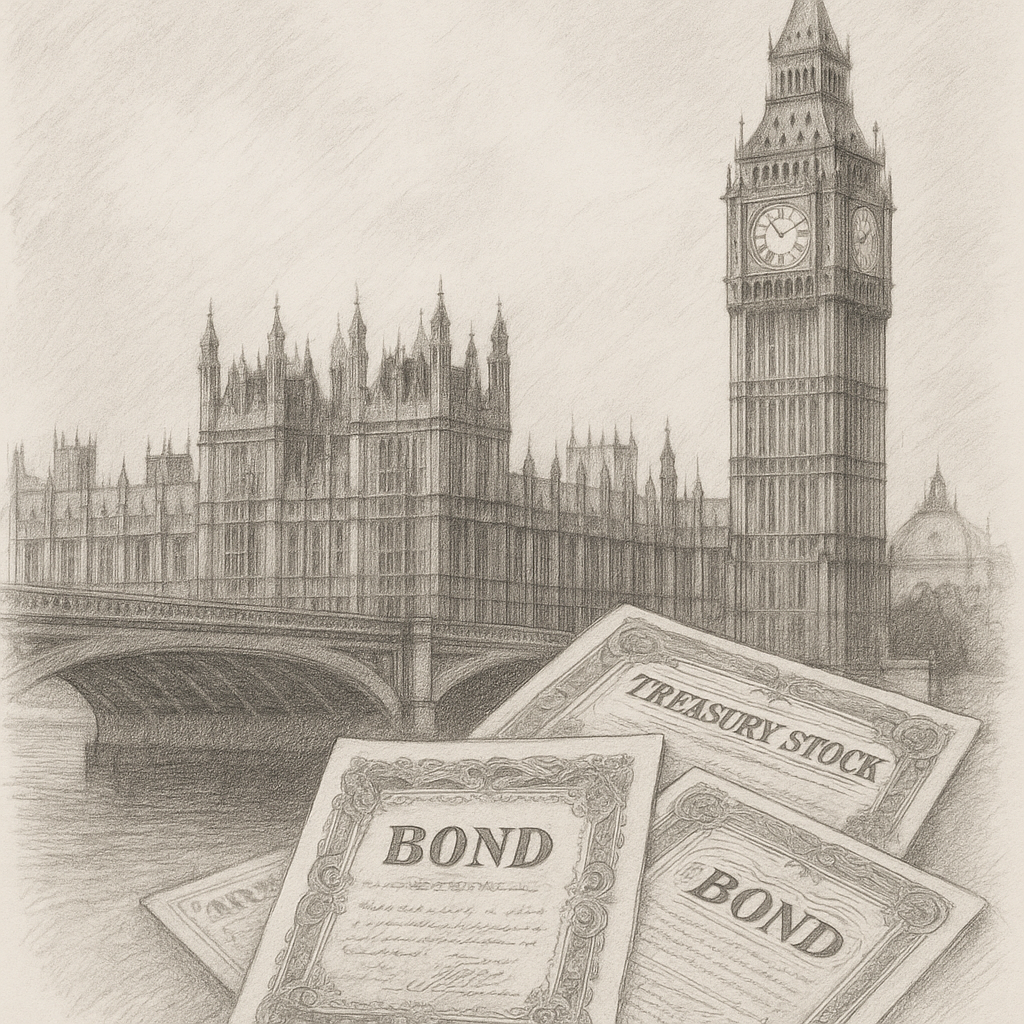国家靠什么取信市场?
1694年的伦敦是个烟雾缭绕的城市:街上满是马粪,咖啡馆里满是消息,议会里满是争吵。当时的英国正在与法国打仗,战争烧钱的速度远超过部长们批预算的速度。然而就在这种一地鸡毛的环境里,一个影响世界几百年的思想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信用并非来自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制度。政府不是靠王权借钱,而是靠制度和治理借钱。
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需要把故事从头讲起。1693 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与法国的九年战争进入胶着期。战争就像一台永不满足的机器,不断吞噬英国的税收、储备和耐心。当时英格兰的财政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寅吃卯粮,靠借债苟延残喘。”政府向伦敦商人借钱,但是远远不够;想通过增税增收,但税负已经将人民逼到民怨沸腾的边缘。
为了应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时任英国财政部大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把国家信用证券化【2】。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很简单,但在300多年前,它绝对是金融创新。政府要想借到钱,就必须让债权人相信这笔钱“可以追索”。追索的对象,不是国王的私人信誉,而是议会作为一个治理体系的信用。
换句话说,英国首次提出:
债务不是国王欠的,而是国家欠的。国债购买者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王权,而是来自议会制度。
这就是著名的“信用革命”。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如果政府赖账,议会负责还钱。”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和创新呢?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政府赖账是家常便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在 1680 年代直接宣布国库破产,拒绝支付大部分战争债券,理由是“朕就是国家”。西班牙王室破产次数多达十几次。所以当时的商人和民众,对于王室的信用完全缺乏信任。任何人如果购买政府发的债券,就要做好政府违约,血本无归的准备。这也导致,欧洲王室想要通过借钱筹资去打仗,他们就不得不支付比较高的利息,来弥补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英国的突破在于,它第一次告诉投资者:能够保障债权人利益和投资不受损失的,不是国王的金库或者诺言,而是议会制度的约束。
1690 年代的英国,正好具备了三个关键条件得以让这样的金融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议会主权。1688 年的“光荣革命”,剥夺了国王随意征税和花钱的权力,财政必须由议会批准。这就好比一个喜欢花天酒地的老公,把银行卡密码交给老婆,从此再也不能胡吃海喝。王权不能乱来,一国财政才有了可预测性。
第二,透明的公共预算。从那以后,英国开始公布年度预算,让债权人能看到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现代财政管理的雏形就此形成。
第三,税收与债务挂钩。1694 年英国《通行税法案》规定,某些税收被专门拨出来用来偿还特定债务。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专款专用”:给债权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这些制度的出现,使得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把公共治理结构包装成“信用产品”的国家。当时的银行家威廉·帕特森一语道破天机:“议会是我们的金矿。”
接下来的1694 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政府与市场共同打造”的中央银行。它不是国王的私人金库,而是一家有股东和资本、能提供流动性的“金融机构”。英国政府向央行借钱,而央行则把债务证券化再卖给市场上的投资者。
这种结构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革命性的。其带来的好处可以直接从数据上看出:从 1694 年到 1705 年,英国政府的长期借款成本从约 14% 降到 6%;而同期法国的国债收益率仍高达 15%-20%【1】。两相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英国制度的巨大优势。尤为重要的事,英国的优势并非生产或者资源优势,而是治理和制度优势。
我们这里说的制度优势,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内被反复挑战,反复验证。举例来说,从18 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债务一路上涨,到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逼近 250%,放在今天足以让任何一个财政部长彻夜难眠。但更惊讶的是,从 17 世纪末至今,英国从未发生过主权违约。制度稳定性本身成了这个国家最宝贵的担保品。
从那以后,英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公共债务体系,几乎都沿用了类似逻辑,那就是通过制度和治理来获取公众的信任,从而让政府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从市场上借钱筹资。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即使债务水平很高,市场也并不担心他们的违约风险,其举债的成本依然被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债务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治理质量差,缺乏制度层面的监督和约束,从而让市场对他们产生无力偿债的担心。
如果我们把制度信用看成一种资产,它具备所有投资资产的特征:比如它有波动性(政治变迁)、有折旧(腐败、治理退化)、有超额收益(制度改革)、也有突然崩盘(革命或者政变)的时候。金融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对一国的制度信用进行定价。
举例来说,2011 年,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僵持不下,市场一度担心“技术性违约”。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在危机期间持续下行,从约 3.2% 下降到 2.5% 左右。原因并不是市场看不见政治风险,而是资金在恐慌中反而回流至美债这个避险资产港,押注的是“制度不会崩盘,治理会把问题解决”的长期预期。
2022 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推出“迷你预算”。由于税减规模过大,该预算迅速击穿了市场对当时英国内阁财政治理的信心。十年期英镑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约 1% 飙升至超过 4%,成为英国三十年来最剧烈的主权债务收益率震荡。市场传递的信号很简单:治理可信度比债务规模更重要。
反观日本的公共债务,占到 GDP 比例长期高于 25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水平。但过去十多年里,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保持在极低区间,直到最近货币政策调整才略有抬升。市场之所以愿意以如此低的收益率购买日本国债,除了日本的通缩环境之外,其治理质量给市场以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些例子说明:一国国债的收益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其制度和治理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国家的债务可以滚,税收可以涨,利率可以变,经济可以波动,但一旦失去制度和治理信用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说 1694 年的英国金融革命教给我们什么,那绝不仅限于一个简单的金融创新,而是一个更深刻的事实:信用从来不是经济产物,而是治理产物。 一个国家能以合理的成本借到钱,不是因为它富,而是因为它可信;不是因为它拥有资源,而是因为它拥有制度。债务危机往往不是从财政部门爆发,而是从治理层面爆发。真正的违约风险,也从不是财政违约,而是治理违约。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资源,而是治理;而治理质量,正是现代信用体系中最重要的底层抵押品。
参考资料:【1】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2】Thomas Levenson, Money for Nothing: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HarperCollins, 2020.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