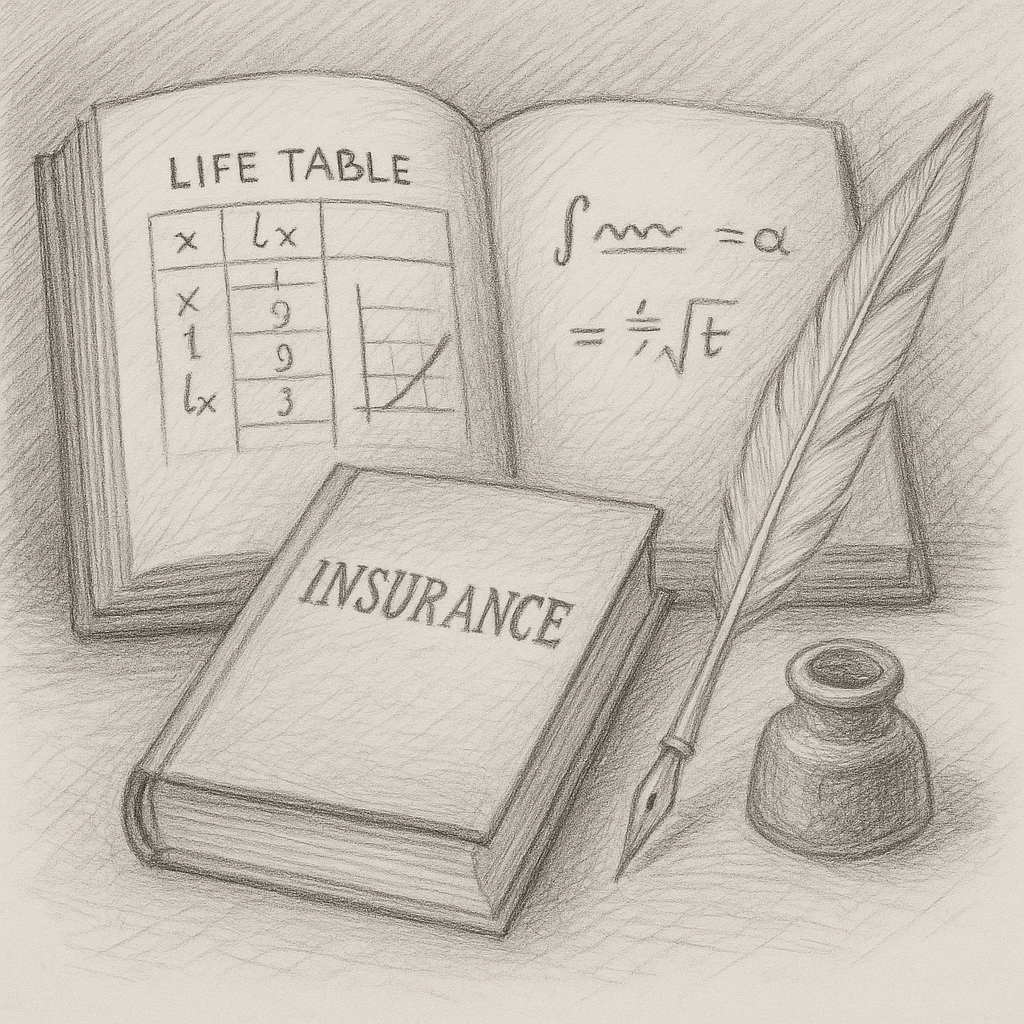精算先到,保险为何迟到半世纪?
在笔者此前写的“从哈雷到AI”一文中,我提到过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在机缘巧合之下,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死亡登记表,上面记录了一个小城布雷斯劳城 20 多年来的出生与死亡纪录。它看上去毫不起眼,却成为精算统计的起点。数学第一次能够量化生命的长短,甚至可以预测人口的变化。
如果说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有趣。在 17 世纪末,我们人类掌握的数学知识,已经可以让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定价寿险。然后寿险真正被商业世界接受,却还要再等上 50 年,直到18世纪中叶。
50 年是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一个国家经历两次战争,也足够让一门科学从新奇变成必需。科学比市场早到了半个世纪,这种延迟并非技术原因,而是人性的节奏。保险业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总按照科学的速度前进,而是常常按照公众的心理速度前进。
要理解这一段延迟,我们必须回到寿命表本身。哈雷在 1693 年整理并发表了《人类死亡概率估算》,首次利用大量死亡数据计算不同年龄段的死亡概率【1】。一个 30 岁男性一年内死亡的概率是多少。5 岁儿童的生存率是多少。80 岁老人再活 10 年的机会有多大。数学首次揭示,死亡虽然不可预测,但并非完全混乱。概率背后存在规律,而规律可以计算。寿险的定价、年金支付、长期储蓄,都有了清晰的科学基础。
按理说,拥有如此精确的死亡概率,保险应该立刻成为大生意。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到处是死亡风险与不确定性。火灾、航海、疾病、战争,无处不是风险。数学已经能准确计算,而风险无处不在。任何有效的市场都应该迫不及待采用这种科学方法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然而,理性并不总是市场的主宰。保险业的真正成熟,要等到整整 50 年以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人类本能地拒绝面对自己的死亡。
售卖保险产品绕不过的一环,是要求消费者在签合同前认真思考自己死亡的情景。死亡概率本身是冷冰冰的数据,但对于任何普通人来说,死亡这个话题带有强烈的情感。正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人类并不擅长处理概率,尤其是那些涉及自身生死的概率。一个 50 岁的人在数学上死亡概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三点几,但如果他恰好刚参加完朋友的葬礼,他心理上死亡的概率很可能在那一瞬间接近百分之一百。数学的平均值无法覆盖情绪的起伏,这就是第一道门槛。
第二,缺乏可信赖的机构和立法。
虽然寿命表能够计算死亡概率,但300年前的市场上,还不存在资金雄厚且能长久经营,让人信得过的保险公司。在 17 世纪末,普通人根本无法相信任何机构能够保证一份长期寿险合同的支付。保险不是短期交易,而是几十年的承诺。一个没有资本金、没有监管、没有信誉的机构,根本无法让公众愿意把钱交给它一生。科学可以解释风险,但科学无法创造信任。信任是制度才能提供的东西。制度尚未成熟时,科学只能停在纸面上。
第三,个体的命运不等于群体的规律。
寿命表揭示的是一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的死亡规律。可是人类无法把自己看成群体中的那一个平均值。科学能够计算一个群体的平均数值,却无法说服每一个真实的个体。保险是一种把个体风险转移到集体层面风险的制度,而人类天生不擅长理解这种风险转移。哈雷的寿命表能完美描述一个城市 20 年内的死亡模式,却很难让一个码头工人理解他自己可能明天就在这个分布里。
正因为如此,科学虽然在 17 世纪末就准备好了,但保险的现代化却要等到 18 世纪中叶才真正出现。伦敦第一批基于精算科学的寿险机构出现在 1740 年前后,并在 1762 年随着 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的成立达到历史性的突破【2】。50 多年过去了,数学、制度与人性终于同时到位。寿险才真正成为一门生意。
这个 50 年的延迟,看似只是保险业内部的事情,但其实它揭示了一条至今仍然有效的规律。那就是科学经常比人类提前到达,而人类社会则只会慢慢跟上。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和制度问题。这种时间差在现实中有很多例子。
比如在2019年以后进入公众视野的mRNA 技术和疫情预测模型,就非常典型。mRNA 疫苗的核心技术,最早在 1990 年代就已经出现。后来到了2005年,匈牙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也是全球 mRNA 疫苗技术的核心奠基者卡里科发表论文,彻底解决了 mRNA 的稳定性问题,使其有可能进入临床应用。科学端已经准备完毕,但大药厂与监管机构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原因不是科学,而是各种疑虑和商业盈利性考量。mRNA 看起来太新,太前沿,储存条件复杂,商业可行性存疑。辉瑞早在 2010 年就拒绝投资 mRNA 平台,认为其前途渺茫。科学端提前了十几年,然而市场端却根本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疫情预测模型也面临类似的规律。流行病学的 SIR 模型在 1920 年代已经成形,现代计算机模型在 1970 年代就能模拟完整的疫情曲线。科学早已具备预测能力,甚至能够量化封锁策略、感染路径与资源需求。但这些模型在日常治理中几乎无人理会,原因依旧不是技术,而是心理和制度。公众根本不相信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个覆盖全球的Pandemic,政府也不愿意去投资准备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的风险。
直到 2019 年,新冠疫情像一道闷棍敲在人类头上,所有原本被忽视的科学突然变成了现实需求。mRNA 技术在几个月内被推向全球,疫情模型也在短时间内成为各国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科学并不是在疫情中突然成熟,而是成熟已久,只是人类直到被现实逼到墙角才选择相信。
气候风险模型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气候科学界在 1990 年代就已经能够用全球气候模型预测温度变化,在 2000 年前后进一步利用高分辨率数据模拟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率以及区域性干旱风险。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些模型在2000 年前后的成熟度已经可以用于长期风险定价,完全可以支持保险费率、房地产估值与主权信用分析。
但金融行业对这些模型的接受速度却慢得多。再保险公司在 1990 年代就能使用基础气候模型,但真正把模型结果写进保费与资本金要求,则要等到 2015 年以后。更严格的气候情景分析普及,则要等到 2021 年之后,保费结构才开始明显调整。银行体系的延迟更加明显。央行与监管机构直到 2018 年才首次在宏观审慎框架中讨论气候风险,全球央行的气候小组 NGFS 在 2019 年成立,而英国央行的第一份气候压力测试框架则在 2020 年发布。换句话说,金融体系真正意识到气候模型与金融稳定的相关性,并在实践中开始应用,只是最近五六年的事。
评级机构的跟进速度也差不多。穆迪与标普在 2020 年以后才第一次把气候风险纳入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信用报告,之前几十年几乎完全忽视长期气候冲击。美国东南沿海房产早在 2010 年左右就被模型标注为高风险区域,但真正出现市场定价折让,却要等到 2021 年,迈阿密部分沿海社区房价首次跌破全市平均估值。
上面这两个例子,与寿险的延迟模式高度趋同。科学提供知识,人类却需要时间才能更充分地理解并应用科学。这些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与概率相关的行业,都必须面对科学与人性之间那段必然存在的距离。这个距离一方面给人类更多的时间来认识并理解科学的价值,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科学应用的时滞。
科学能为未来点一盏灯,但社会何时迈步,却常常自有节奏。保险如此,气候模型如此,mRNA 技术与公共卫生同样如此。真正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质量的,除了科技本身,还需要制度跟上,并且公众被说服和接受。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的准备总是提前,而人类的行动往往在需要真正出现时才渐渐跟上。这样的距离,也许正是文明向前推进的方式。
参考资料:【1】Edmond Halley, An Estimate of the Degrees of the Mortality of Mankin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1693【2】Thomas Levenson, Money for Nothing, Harper Collins, 2020
免责声明: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